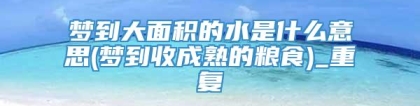望断天涯不见鸿,丢魂落魄三日兮;恍若隔世一场梦,落入土堆野草凄。-----题记。晚十点,夕阳未落的小院里,十二棵葳蕤的梧桐树梢,停满了叽喳聚会的小麻雀。在一棵树上跳跃欢唱,在几棵树间游玩穿梭、在空中盘旋舞蹈、在地上踢踏捉迷藏,这是每个夜幕前的欢场,也是一对杜鹃鸟躲在格檐处呢喃的旧时光。我远远看着,静静听着,拉近镜头捕捉到杜鹃鸟情侣之间的互动。一只灰黑色饱满,一只灰白色纤柔。他们并排站着,保持几寸之隔的距离,时而相望,时而眺望远方、时而低眉轻啄木头、时而搔首抚弄羽毛。翻看为杜鹃鸟拍摄的写真,猜想他们是一对左手摸右手的夫妻,没有太多的甜言蜜语,缠绵依依,宛如这几日大漠送来的微风,悠然和煦。随着一群麻雀惦着身子在地上扑腾,才知道一只羽翼未全的麻雀瘫软在地,树上的麻雀们沸腾起来,树间的麻雀更是慌了神,在高空,低空盘旋呐喊。我上前,吓飞了一群无措的小精灵,留下那只不会飞翔的幼雀。我也失了主意,咋整?这只大手怎敢触摸那肉肉的小躯体,又怎能攀爬上树,送她回巢?四周雀语漫天,看着轻轻蠕动的雀儿,想着从那么高的树丛间摔下来,定是伤了四肢。我不是医生,不懂怎么救治,更不敢去挪动她软软的身子,只能叨叨蹩脚的普通话与众鸟儿对话:“鸟儿,鸟儿,别害怕,我不是坏人,不会伤害你们,等我想想办法,送你们的幼崽归家啊”。婆婆远远提醒:“弄点面糊糊,先喂喂”。是个办法,先喂喂,我一步三回首,看着那个小不点,跑进厨房,舀几勺糊糊回来。空旷的水泥地上,不见了幼鸟,树上的麻雀们也没有先前的忙碌与喧嚣,难道幼鸟归巢啦?他们平日里用嘴巴筑巢,孩子们跌落受伤定是雀妈妈,雀爸爸衔回家疗伤了吧。纤风曳曳入花间,花语幽幽如歌令。那对情侣杜鹃鸟不知何时停驻在屏风的栏杆上,或许是麻雀儿落地时,或许是麻雀们无助时,或许他们参与过救助。他们是同类,懂得同胞落难时的疼痛,亦懂得如何医治疗伤。虚惊几许,幼鸟得救,一家团聚,大家齐聚,甚是欣慰。不去打扰,保持距离,或许是最和谐的相处方式,任树叶间此起彼伏,序然着一场众鸟的盛会。七月已经老去,而我耳边仍旧响着六月的雀语,提着蒸腾的裙袂,等待八月的凉风,吹落脚裸的花瓣,记一纸吐墨含香的故事。剧情可随笔端流淌,也可逆转回旋,奈何现实我只能用悲凉一笔带过,夺食的刀刃在柔弱的苍生身上,生命脆弱,微尘不足。还未等到夕阳褪去光芒,不经意地抬眸,看见花坛里玫瑰花间挂满了羽毛,走近,有带血的肉毛,有残存的骨骸......。有些惊慌,我赶忙打电话询问:“一只杜鹃鸟好像被什么残害了,会是谁?”。“可能是猫头鹰吃了”,电话那头先生急促解释。“猫头鹰不是只抓小鸡吗,这像是我前几天拍过照片的那只灰白杜鹃鸟呢”,我追问。“猫头鹰吃小鸡当然也吃鸟啦”,那边飘来不耐烦的声音。“猫头鹰和杜鹃鸟都是鸟类,干嘛要残忍吞食啊?”我紧追不舍。“大鱼吃小鱼,小鱼吃虾米,你没听说过吗?二憨,忙着呢,挂啦”。弱肉强食,奈何轻喟声声。我找来纸盒,拾起残体,如往去找锄头,在那棵梧桐树下,挖一个坑,拾起几捧残花,掩土埋葬。又想起去年冬天的那个傍晚,我在车间里埋头加班时,被剧烈的碰撞声吓着,就那么几声停止后,外面平息无声,就没起身去看,继续着手头的工作。隔日,我路过窗台,发现一只猫头鹰躺在地上,已奄奄一息。回想前晚的响声,才知道是猫头鹰撞在铁柱子上往生了。唏嘘之间,糊一方纸盒,在葡萄树下,挖一个坑,找一些枯叶保暖,把猫头鹰深深掩埋。如今,那只灰白色杜鹃鸟长眠于此,是否被猫头鹰残害了,不得而知。而我,只能用这样的方式祭奠她的今世,祝福她的来生。那只灰黑色杜鹃鸟接连三日站在窗台上,痴痴的望向那堆土包。当日,我没太在意,以为是某鸟儿来院子里串门。翌日,天色渐暗,他仍然站在窗台一动不动望着梧桐树下的土包。仔细看才发现是那只灰黑杜鹃鸟,土包下可躺着他的伴侣呢。想着他一连两日不吃不喝,不眠不休,便拿一把小米过去喂。他见我走近,跳下窗台慢悠悠踱着步子与我背道而行,知道他在躲避我,索性把小米撒在台阶上,离开,远观。这个夜晚,我失眠了,担忧那只灰黑杜鹃鸟熬不住而倒下,这个院里我掩埋过好几只鸟儿,亦如他的妻子。不忍遐想太多,但总会让我愁绪一阵子,在漫漫的长夜,在毫无睡意地尽头。次日的晨曦,窗台上,他没有倦意,仍直愣愣望着那堆土包。看来,我的忧虑多余了,他没有饿晕倒下。走近去看台阶上的米粒,还是散花状,他不饿吗?我与他保持距离,绕道走进厨房,想把这只杜鹃鸟的痴情讲给婆婆听。端着婆婆熬的小米粥出门,听见划过院子的几声“咕咕咕”啼鸣,像是那只杜鹃鸟,又像有几只接应“咕咕咕,咕咕咕”。等我望向窗台时,他飞走了。花坛里,玫瑰花丛间,是那只灰白杜鹃鸟绝命的地方,我已翻新了土壤。每个夕阳落晖时,那只灰黑杜鹃鸟还是会来,在池子里喝水,在土壤里轻啄,扑腾扑腾飞走,又不声不响落在窗台,望着那堆土包发呆。苍生有情,万物有灵,都在等什么?有的等白昼,有的等夜临;有的等雨来,有的等风去;有的等爱回,有的等情归。来生,荷花池里重相逢,她粉红洁身,端然安素;他淤泥护身,慈悲祥和。吴婷梅,湖北宜昌人。省作协会员,宜昌市影视家协会会员,微旬刊《大文坊》编委兼“人物坊”主编。作品散见纸刊和诸多网刊。